男女主角分别是李强小吴的其他类型小说《818之后的西哈努克城李强小吴小说》,由网络作家“是名为心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个长期客户,他懂得分寸、会说话,熟悉规矩。他也曾梦想过,在这片“南洋淘金地”熬出头来,攒够钱回南宁开家大排档,安稳度日。可禁赌令像一记闷棍砸在所有人的后脑。短短三个月内,八成赌场关门,中国人走得像潮水般快。老板走得最快,卷钱消失,只留下断水断电的宿舍楼和一地狼藉。陈明被迫搬出宿舍。他拖着一个皮箱,走了七公里,最后在“中柬商城”旁一个被废弃的火锅店里落脚。那个地方本来是中午最热闹的一条街,如今只剩下风吹招牌咯吱响。起初,他靠翻译打零工维生。但市场实在太冷,来的人少,活儿也少。他不甘心,总觉得西港还没死透。一天,他路过一堆工地废料堆,看到几根废钢筋和油桶,突然灵光一闪。——不如开个面摊吧。说干就干。他把油桶锯开改成灶台,从旧市场淘了些桌...
《818之后的西哈努克城李强小吴小说》精彩片段
个长期客户,他懂得分寸、会说话,熟悉规矩。
他也曾梦想过,在这片“南洋淘金地”熬出头来,攒够钱回南宁开家大排档,安稳度日。
可禁赌令像一记闷棍砸在所有人的后脑。
短短三个月内,八成赌场关门,中国人走得像潮水般快。
老板走得最快,卷钱消失,只留下断水断电的宿舍楼和一地狼藉。
陈明被迫搬出宿舍。
他拖着一个皮箱,走了七公里,最后在“中柬商城”旁一个被废弃的火锅店里落脚。
那个地方本来是中午最热闹的一条街,如今只剩下风吹招牌咯吱响。
起初,他靠翻译打零工维生。
但市场实在太冷,来的人少,活儿也少。
他不甘心,总觉得西港还没死透。
一天,他路过一堆工地废料堆,看到几根废钢筋和油桶,突然灵光一闪。
——不如开个面摊吧。
说干就干。
他把油桶锯开改成灶台,从旧市场淘了些桌椅,又到附近华人店里低价收了些面条调料。
三天后,一个不起眼的“陈记牛肉面”摊子在“东方壹号”旁的空地上冒起热气。
第一锅面,卖给的是修空调的两个本地人。
他没想到对方吃完直竖大拇指:“Good!
Very good!”
后来,那两人带来朋友,朋友又带朋友,渐渐传开。
来吃的有民工、散户、小贩,甚至还有几个柬埔寨警察。
一碗五千瑞尔,不贵,但热乎,香气四溢,在西港这个“冷城”里成了罕见的人气所在。
不久后,一个熟人来了——李强。
“哟,李工!”
陈明笑着打招呼,“尝尝我的牛肉面,保你回味三天。”
李强一口干了汤,点头:“真不错,你这算是给西港续命。”
“哪儿啊,活下去而已。”
陈明抽了支烟,递给李强,“说吧,你啥时候也不跑了?”
“早就决定不跑了。”
李强笑笑,“你不是也没跑?”
他们没再多说话,但彼此心里都明白:留下的人,不是没选择,而是愿意再赌一次。
面摊逐渐有了点气象。
陈明将店面从三平米扩到十平米,弄了块布招牌。
夜晚时,他常点上几个露营灯,一边放着手机里的粤语老歌,一边煮面。
有时候,索菲亚也会带游客来吃,他笑着递上筷子:“正宗中柬融合美食,不辣不要钱!”
他还收了一个徒弟,一
叫住了她。
“你是……那导游?”
她回头,看见一个瘦高的中国人,满脸晒痕,穿着旧反光马甲,正站在一堆钢筋边擦汗。
他自我介绍叫李强,是“海蓝之城”的前项目负责人,现在还在这里“守着点事”。
“这儿还能建吗?”
索菲亚有点惊讶。
“能建,为什么不能?”
李强笑了笑,“房子空着也要维护,总不能让它塌了砸人。”
“可没人住了。”
李强沉默片刻,然后说:“那我们就建给还留着的人住。”
这句话,让索菲亚在心里微微一震。
她没有继续带团,而是留了下来,帮李强做一些翻译。
李强需要和本地工人沟通,她的柬语和中文都很流利,便成了最合适的桥梁。
从那天起,两人渐渐熟络。
他们一同巡视楼层,查看地下水管线是否堵塞,一起去废弃工地清理被弃置的材料。
有一次,两人冒雨去“金达大厦”拆旧门窗回收,那场雨下了三个小时,索菲亚冻得直哆嗦,李强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。
她笑着说:“你不怕我跑了吗?”
李强耸肩:“你连西港都没跑,我怕什么?”
那晚,他们坐在半封顶楼的天台上,喝着本地啤酒。
夜色如墨,城市安静得出奇,远处还能听见海浪的声音。
“你说,”索菲亚开口,“这地方真的还有未来吗?”
李强点了根烟,静静地说:“只要还有人,还在呼吸,这里就不是末日。”
她侧过头,看他眼里映着一点点灯光。
她想起林涛也说过类似的话,但那是五年前。
而现在,说这话的人,正陪她一起在废墟中活着。
这城市虽然死了,但人还活着。
他们就是这片荒原上的火苗。
3陈明第一次想到要离开西港,是在“金象赌场”彻底关门那天。
那晚,他独自站在门口,看着闪烁多年的霓虹牌匾一盏盏熄灭,整栋大楼像死去的怪兽。
玻璃反光映出他苍白的脸,那一刻,他意识到:他所依赖的世界,已经完结。
三年前,陈明从广西来到西港,最开始在赌场做客服,后来因为嘴皮子利索,当上了公关,负责接待中国贵宾。
赌场是座不夜城,光怪陆离,每天都有无数钱从牌桌上飞起、落下,许多人因此一夜暴富,也有人身无分文、悄然离开。
陈明混得不差。
手上有几
开始还亲自守门,但到了第七天,干区的人数突破一百五十,他只能退到“协调岗”,由皮萨和另一名青年来管理进出。
“再这么下去,我们自己都吃不饱。”
陈明皱着眉头。
“我不是不想帮。”
他在临时会议上说,“但一锅饭总共就那么大,分太多了,连汤都没味。”
“我理解。”
李强说,“所以我们必须设立‘临界线’。”
“什么线?”
索菲亚问。
“人口线、安全线、资源线。”
林涛解释,“干区能承载的,不是无限的。
如果超了,就不叫秩序,是拖垮。”
老李点了点头,“我是支持限人的,咱这不是慈善会,是活命区。”
最终,他们拟定了“干区守则1.0”:每户最多五人,统一登记。
每人每周必须参与一次公共事务——打水、清扫、维修、烹饪、巡逻等。
新人进入,需两人担保。
严禁盗窃、斗殴、私设火源,违者逐出。
那晚,干区墙上贴满了守则,白纸黑字,翻译成柬语和英文,糊在每栋楼下。
一时间,“西港干区”成了传奇。
有人说这是南洋废城里的“微型乌托邦”,也有人讥讽为“废墟里的秀场”。
但不管外界怎么看,至少在干区里的人知道:他们正在活下去——靠规则、靠电、靠锅里的饭,也靠彼此。
可每一个秩序的建立,都会引发新的不满。
西港西侧有一个区域,原本是“富海广场”楼盘,现在成了几个小帮派的栖身地。
他们不认可干区的规则,也不愿意“登记换饭”,反而盯上了干区逐渐聚拢的物资。
第一起冲突是在凌晨两点。
陈明的第二摊位被砸,锅碗瓢盆撒了一地,挂着的太阳能灯也被砸坏。
两个夜巡的年轻人被打伤,棉布睡棚被点了火。
“他们是故意挑衅。”
林涛断言,“这是警告,也是试探。”
“来头不小。”
老李说,“这些人我打听过,有的是之前赌场保安,有的是‘保护伞’的亲戚,之前就专干收债和清场的活。”
“那我们怎么办?”
皮萨问,“报警?”
李强苦笑,“西港现在连警察局都搬走了,谁来管你?”
那晚,干区召开了首次“危机会议”。
“我们不能指望外部,我们得靠自己。”
李强说,“我们不是要对抗谁,而是要守住我们这一小块地。
守不住怎么办?”
陈明问。
“那就搬。”
索菲亚说,“哪怕只剩一栋楼,也要保住这股子气。”
林涛抬起头,“我们可以设置警戒点,布明哨暗哨,限制夜间出入。
再设一套信号系统,用灯光闪烁表示情况。”
“你还想搞防空预警?”
陈明挤眉弄眼。
“不是开玩笑。”
林涛认真道,“这次他们只是试探,下一次可能直接来抢物资。”
最后,大家达成共识:设立“红线”——干区北侧三百米以外为缓冲带,非登记者进入,视为敌意行为。
与此同时,索菲亚牵头联系了几个仍留在西港的志愿组织,希望得到一些医疗物资和净水片。
她知道,这不仅是保命,更是传递给外界一个信号:我们在努力活着,别让我们死得悄无声息。
然而风暴,在悄然酝酿。
富海广场的一栋大楼,挂上了一面红布条,写着五个中文大字:“干区不得越界。”
那是挑衅,也是宣战。
李强看着那块布条,沉默许久,只说了一句:“我们要准备应对真正的危机了。”
而此时,西港港口附近,一个身份不明的中年人接过卫星电话,用柬语说:“西边那群中国人,开始想建国了。”
对方笑了笑,回答:“那就让他们尝尝建国的代价。”
7黎明前的雨,总是特别冷。
凌晨三点,李强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
他穿上外套冲出保安室,就看到皮萨浑身湿透,脸色苍白。
“北侧,富海广场那边,有人冲过来了……五六个,有刀。”
李强心里“咯噔”一声。
他第一时间吹响巡逻哨,一连串短促的哨声划破夜空,如同旧时代战壕里的紧急集合令。
干区的人从睡梦中惊醒,几乎是本能地穿衣、集合、各就各位。
这是他们过去十天反复演练的应急程序——他们从来不敢真的相信会用上。
灯一盏盏亮起。
电,是这片区域里最有威慑力的信号。
林涛打开了“闪光警报器”,一连串红色频闪灯照亮了北侧三栋楼之间的通道。
“陈明守西侧厨房,老李你去水塔那边。”
李强一边发号施令,一边冲着林涛喊,“你控制电,必要时断后街的照明。”
“明白。”
林涛拉下头灯,戴上手套,走进配电间。
索菲亚已经穿上雨衣,在疏散靠近边缘的住户。
她身
为留下的建筑,留下最后的尊严。
几天后,城市开始沉默。
街上的店铺陆续关门,霓虹灯逐渐熄灭。
赌场外围堆满了废弃的赌博机和破损家具,像一场失败派对的残骸。
街角的小吃摊连夜搬走,中文招牌一个接一个被拆下。
而在这衰败之中,也有一些人选择留下。
比如住在“新龙大酒店”旁边的陈明,曾是赌场的公关经理,如今改在废墟边支了个小灶台,卖兰州拉面。
又比如在“金塔商城”后面的索菲亚,一个柬埔寨女孩,每天带几名西方游客走街串巷,讲述西港如何从繁华到崩塌。
某天傍晚,李强独自走在城市边缘的未开发区,一座座封顶未久的楼房像沉睡的巨人,排成整齐的阵列。
他在其中一栋楼的入口发现了几名本地民工在里面搭了帐篷。
“干嘛的?”
他问。
“住着呗。”
一个年长的柬埔寨汉子笑着回他,“没人管,我们就住。
反正这些楼也没人用了。”
李强没赶他们,反而坐下来和他们聊了很久。
这天夜里,星星出奇地亮。
李强躺在“海蓝之城”的顶层,看着这片荒芜的城市,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安宁。
繁华是短暂的,但废墟却可能孕育新的秩序。
“如果真的要完,”他喃喃地说,“那至少,也得完得像样点。”
于是,李强决定留守。
他开始逐一检查每一栋尚有结构价值的楼房,封锁危险区域,召集留在城中的工人、居民和商贩,自发成立了一个“西港共建小组”。
他们没有资金,没有官方背书,只有一点点技术、几台旧车、一点剩下的水泥和钢筋,还有不愿放弃的信念。
“我们不能建回原来的西港,但我们可以建一个新的地方,一个给活着的人住的地方。”
李强说这话时,声音不大,但谁听了都认真地点头。
末世不是一夜之间降临的,它是一点点凋零,一点点遗忘。
可希望,也是悄悄发芽的。
在这片灰烬之中,李强点燃了第一盏灯。
2索菲亚从不承认自己是个导游,哪怕她每天带着外国游客走过西港的烂尾楼区,讲述这里的起落荣枯。
“我是讲故事的人。”
她在一次旅客拍照时笑着说。
这女孩二十六岁,有着典型的高棉面孔,皮肤小麦色,眼神却很深,像是看尽了岁月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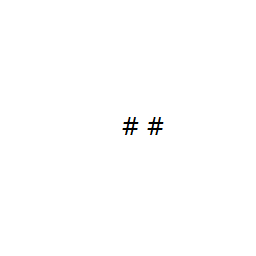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