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夏之白解敏的女频言情小说《爆改大明全文免费》,由网络作家“一两故事换酒钱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李善长的声音小了下来。秦朝历史上是什么结果,他们这些官员又岂会不知,二世而亡,难道大明也会二世而亡?这不太可能。以朱标的治理手段,大明怎么都不可能落到二世而亡的情况。而陛下为子孙后代做的事,的确跟始皇帝相似,都以为按着自己的想法,天下便能固若金汤,大明基业子孙后世无忧。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只是当今陛下太过强势,容不得任何人忤逆,稍有不满,便兴杀伐打骂,因而如今已很少有人劝谏。都依着陛下喜好。汤友恭目光微动,作为都御史,他对这些话是深有体会,陛下的确不喜他人劝谏,也只听顺耳的建议。很多事都喜欢亲力亲为。不喜欢听别人的想法,更喜欢自己提主意,提想法,然后让百官去充实那些主意。士农工商兵中,相较于士工商,陛下的确也更注重农兵。农相关自始自...
《爆改大明全文免费》精彩片段
李善长的声音小了下来。
秦朝历史上是什么结果,他们这些官员又岂会不知,二世而亡,难道大明也会二世而亡?
这不太可能。
以朱标的治理手段,大明怎么都不可能落到二世而亡的情况。
而陛下为子孙后代做的事,的确跟始皇帝相似,都以为按着自己的想法,天下便能固若金汤,大明基业子孙后世无忧。
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只是当今陛下太过强势,容不得任何人忤逆,稍有不满,便兴杀伐打骂,因而如今已很少有人劝谏。
都依着陛下喜好。
汤友恭目光微动,作为都御史,他对这些话是深有体会,陛下的确不喜他人劝谏,也只听顺耳的建议。
很多事都喜欢亲力亲为。
不喜欢听别人的想法,更喜欢自己提主意,提想法,然后让百官去充实那些主意。
士农工商兵中,相较于士工商,陛下的确也更注重农兵。
农相关自始自终都被各种强调,各种做调整,而在兵方面,也不例外,多次兴兵,行廷狱杀戮。
至于士工商。
若非朝廷缺官员严重,以及大明已经坐稳了天下,加之之前地方学室兴建多年,该到出成绩的时候,不然科举重开恐还要一些时日。
而工商方面,则完全依循着龙生龙、凤生凤的鱼鳞图册,严格限制,也严禁自由的变通。
朝臣提过建议。
只是最终都被否决了,因为陛下只相信自己能接受的,除非真到不得不变时,不然陛下都不会轻易去动。
骨子里。
当今陛下就是个农人。
根本没有坐天下的心思,一心只想当个守财主,一旦触及到陛下不擅长的领域,陛下就会生出很大的抵触心理,也不愿轻动。
这些话胡惟庸、杨宪等臣子,私下都有吐槽过,在大明刚立国时,还有臣子劝谏过。
只是无一例外都死了。
久而久之。
也就无人敢再劝了。
眼下大明很多臣子,乃至士人,都只想顺着陛下的心思,等着殿下朱标日后即位,再来斧正一些乱政。
只是他们也没想到,这些东西会被一个科举的举人说出来,还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。
朱标双眸微冷。
对于这人这么评价大明的国政,这么中伤自己的父皇,他为人子,又怎么可能没有怒气。
只是有些话,虽然难听,但也不得不承认,的确是大明存在的问题。
自己的父皇,自一统天下之后,就很难再听取他人的建议了,也自信的有些刚愎自用了。
尤其是在遭到胡惟庸的背叛,还有母后的病逝,父皇已越发不愿相信其他大臣的话了。
这一点。
他也察觉到了。
还跟朱元璋争吵过数次,只是朱元璋性情很执拗,很少会真的去改,而且让开国之君去认错,本就很强人所难。
也不现实。
当下大明的朝政,基本是朱元璋个人想法的一言堂,而后他在自作主张的做些调整,父子也就这般维持着朝政上的默契。
但他面临的压力却是与日俱增。
父皇越来越强势了。
朱标双眸微阖,眼中闪烁着缕缕寒光,他在心中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想将这份‘反文’呈上去。
借此激怒父皇。
同时让父皇意识到问题,从而为大明朝政的改变做一些尝试,至少大明的国政该做出一些调整了。
至于这人的死活。
朱标不在意。
当这人写下这份‘反文’时,他就已经死了,现在只是在将这人的利用价值最大化。
若是能让父皇明白到自己当下出的一些问题,这人就已经算是死得其所了,可以只诛三族。
朱标在心中暗暗盘算着。
殿内死寂。
已经没人敢轻易出声了,不少官员更是直接屏住了呼吸,唯恐会因为自己弄出声响,引得朱标动怒。
朱标收起心神,嘴角噙着一抹冷笑,漠然道:“韩国公,继续念,这些话虽刺耳,却也的确有几分道理,我还不至于生气。”
李善长目光微异,连忙点点头,道:“洪武帝在位多年,对天下的实际治理,都只作用于表面。”
“换句话说。”
“只是在对天下进行一定的缝缝补补,并未对天下做到讨元檄文说的那般通彻盘整。”
“相较于过往朝代,明立国以来,可有切实的安民之策?可有富民之政?可有强国之谋?”
“未尝有也。”
“大明这些年更多的是在算计着民众的口食,上至王公大臣,下至黎庶竟皆如此。”
“明之策,出发点只有一个。”
“活人却不能养人。”
“以此才便于天下臣民,世世代代为明之宗室,辛劳贡献,以换取养人的资格。”
“然为君者,主长策者,当殚精竭虑于国之大事,以民生为要,以天下为本,发展民生。”
“寻亩产千斤之粮,创日行千里之铁马,斩敌万里外之火龙,呼风唤雨,掌控天地万象。”
“如此方为泱泱大国。”
“方能定鼎天下,去谋万世之国。”
“若始终不思进取,只盯着那点旧有的坛坛罐罐,终会将天下带入歧路,到那时,天下只会重复老路。”
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!”
“明得天下是因得民心,如今的大明,却是在不断失民心,当民心尽失之时,便是天下揭竿再起之时。”
“那时会有人替大明挽天倾吗?能够挽天倾吗?”
“不能。”
“因为明不爱民。”
“失了民心,又格外提防着天下官员,何以让人敢为明去抛头颅、洒热血?”
“粉色全无饥色加,岂知人世有荣华。年年道我蚕辛苦,底事浑身着苎麻。”
“朱家的天下又跟百姓何干?”
李善长将这篇反文一字不漏的念完了,随即轻轻的将这篇试卷合上,静等着朱标开口。
吴公达、郭翀等官员,依旧战战兢兢的跪在地上,面色苍白,毫无半点士人风骨尊严。
汤友恭、赵瑁等人,同样低垂着头,一言不发,心中却是冷笑连连,作文之人,太想当然了。
以为洋洋洒洒的写篇针砭时弊之文,直接反对大明国政,抨击陛下,就能让陛下殿下另眼相看。
纯属想太多。
只顾着心中畅快,等刀斧加身,祸及亲族时,再想痛哭流涕,跪地求饶也为时已晚。
愚不可及。
当今陛下可是从尸山血海闯过来的,最不怕的就是杀人!
当考场其他的举人考生还在斟酌如何落墨,如何在策问上,展现自己的治政才华时,夏之白已在宣纸上挥洒自如了。
半晌。
夏之白停下了笔,他吹了吹上面未干的墨迹,简略的看了几眼,满意的点了点头。
他知道。
自己写的的这‘问策’卷交上去后,定会震动整个礼部,甚至是整个天下,他也将因此名动京城。
只是出的哪个名,他不清楚。
也不在意。
来到大明,见到了当代这么多的残暴不仁,黑暗潦倒,心中早就只剩下一个念头了。
就是要改变历史的进程。
虽然这是大明,古代封建专制制度顶峰的大明,还是在洪武朝。
但他不在乎。
穿越一场,总该为天下做点什么,总该要有舍我其谁的气魄。
他的选择,是跟历史上的先辈们站在同一队列,或有歧路,但只要最终目的达成,那便是一条康庄大道。
他来,便只为爆改大明!
如若不成,葬身在这腐朽的旧社会,也不会有任何遗憾跟愧疚。
他来过,抗争过。
便已足矣。
夏之白抬头,望着高窗透过的阳光,突然想起了过去在《建军大业》中看到的一句话。
“那些被战火洗礼的灵魂,将同人民的命运,融在一起,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……”
“无上光荣!”
如今。
他渐渐领悟了这句话。
他垂下头,眼中闪烁着亮光,胸腔满腔的热血在流淌,道:“死者的意义是由生者赋予的,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,同样无上光荣!”
夏之白嘴角掠起一抹笑容,继续在宣纸上写着,对朱元璋而言是反文的‘策问’。
“……”
“洪武帝起于微末,看似最体恤百姓,实则对民也最为肤浅。”
“对天下之民,无天下之见。”
“洪武帝空有爱民之心,实无爱民之举,据天下为私有,假以爱民之举,行虐民之行。”
“视百官为长工,视万民为家奴。”
“……”
夏之白并未一味的抨击。
他参加科举,并不是为宣泄对当代的不满,也非是愣头青一般的义愤填膺,而是真切的想改变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,虽言辞中多有不敬,但更多的还是恨其不争,自甘堕落。
晌午。
会试第三场到点。
夏之白的‘策问’早就写完,也提早将考桌上的宣纸整理完毕,听到一声清脆的‘金’鸣响,便直接起身将试卷交到了门口收卷官手中,顺着大流出了文墀宫。
文墀宫外。
夏之白站定,回头看了一眼。
他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笑容,坚定的道:“面壁十年图破壁,难酬蹈海亦英雄。”
“这一次。”
“定要在这浑浊世道闯一遭。”
夏之白回过头,看了眼四周,朝着贡院内自己居住的号舍走去。
会试考场是在文墀宫,而会试跟乡试一样,三天考一场,共三场,因而在这九天内,他们都只得待在官府安排的号舍里。
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
而且吃食这些还得自己准备。
官府并不提供。
如今三年一次的会试,已暂告一段落,后面的评卷也由不得他们,他们自是到了该离场的时候。
科举发榜一般在科考完十天后,在这十天内,他们需自找住处,不过身为举人,自不用这么麻烦。
早就有先期到京师做官,或者地方商贾们集资在京师购置了房产,当做地方的集会会所,而在明朝这个会所则被称之为‘会馆’。
京师五方所聚,其乡各有会馆。
应天府内修建的大多数会馆,主要为同乡官僚、缙绅和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居停聚会之地,以地域关系为基础,既方便了人员的管理,也为先期为官的上位者积累了声望人脉。
因而一直被人热衷。
夏之白随身携带的行李并不多。
就一些吃剩的干粮,还有一些换洗衣物,简单收拾了一下,背着行囊就走出了号舍。
号舍外此刻人声鼎沸。
随着最后一场考试落幕,压在众人心头上的大山,一下被卸掉了,原本还沉默寡言的众人,此刻也变得活络起来。
只是相较大多数人的活跃,夏之白等人却显得较为沉闷,因为活跃的考生大多出自南方。
他们人数众多。
而且自科举以来,就向来不把北方考生放在眼里,话里话外都充斥着对北方考生的贬低跟奚落。
无他。
南强北弱。
这已不是一年半载了,而是有不少的光景了。
大明自开科举开始,科举取士中南方考生的数量,都远远高于北方。
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的三人,也一直为南方学子牢牢霸占,从未旁落。
赐进士出身的第二甲,大多数也是南方考生,北方考生通常只能在赐同进士出身的第三甲名录中,才会有他们的身影。
加之浙江淮西势力在朝中极大,更是让这些南方学子得意,对北方学子更是多有不屑。
夏之白刚到应天府时,便听到了外面传的童谣。
黄练花,花练黄!
黄是指黄子澄,练是指练子宁,花是指花纶,而在这些童谣中,这三人似是上天注定,定要位列前三的。
只是名次或稍有变动。
令夏之白惊奇的是,这个童谣不仅被广为流传,而且还被参加科举的其他考生认可,也都一致认为状元榜眼探花定是出自他们三人。
这也足以看出,这三人的文学才能是远胜于其他人,不然不至于被这么多人追捧跟认可。
“黄兄,这次新科状元恐是非你莫属了吧?”
“哪里,花兄谬赞了,依我看还是花兄跟练兄更胜一筹,跟二位的才识一比,我也就能当个探花了。”
“黄兄,你又打趣我不是,城中传了这么久的黄练花,花练黄,我练子宁可是一次都没跑到前面。”
“这状元怎么都轮不到我。”
黄子澄、练子宁,花纶三人互相打趣着,嘴里都在互做恭维,但眼里都流露着势在必得的雄心跟斗志。
对于新科状元这个头衔,他们三人私下明争暗斗了许久,不想当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这可是大明科举停考十年后的第一个状元,上万名举人一同参加的科举,意义非凡。
他们怎么可能不动心。
黄子澄看了看四周,目光一动,大声道:“花兄,练兄,我若没记错,上次科举,朝廷取士一百二十人,南方士人八十几人,北方不过三十出头。”
“经过这十年休整,两位认为这次北方会有多少人位列三甲?”
花纶看了黄子澄几眼,又瞟了几眼一旁敢怒不敢言的北方学子,嘴角露出一抹轻蔑,道:“只怕会不足南方的三分之一。”
“北方跟胡虏搅和太久,早就失了文心,一群未受过太多文学洗礼的人,就算再给十年又有何用?”
练子宁附和冷笑道:“依我看,二甲取士都不一定会有北方考生,有也是末端。”
黄子澄点点头,认同道:“北方终究跟我等不同,离蛮夷太近,离先贤大家太远,或许他们现在已经不适合读书研究学问了。”
三人你一言我一句,也是引得四周一阵大笑,还有一阵叫好声,唯有北方学子一脸阴沉,却无可奈何。
因为的确考不过。
夏之白看了眼众星捧月的三人,眉头一皱,就在这时,一道声音却是从一旁传来。
“夏老弟,你考得如何?”
郭翀的话一出,原本还有说有笑的众人面色陡然一滞,李善长更是连忙出声怒喝道:
“郭侍郎,休得胡说八道。”
“我大明朝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之传承,为万民爱戴,岂会有人在科举考时写反文。”
李善长一脸阴翳。
反文,这可不是小事,尤其还是在新开科举的节骨眼上,陛下本就略对士人不喜,要是出了这种事,只怕会严重影响到日后的科举取士。
他岂敢不重视?
吴公达狐疑的看了眼郭翀,他了解郭翀的为人,是有些心高气傲,但这种口误还是绝不会犯的。
尤其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
而且这可是科举,对天下士人而言,一步登天的机会,耗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,就为在这时写一篇反文?
这是不是太荒唐了?!
朱标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铁青,他冷冷的看着郭翀,沉声问道:“郭侍郎,你说你审阅到了一篇反文?”
“当真如此?”
郭翀跪伏在地,头几乎贴在地上,咬牙道:“回禀殿下,臣……臣的确看到了一篇反文。”
“臣不敢说谎。”
四周死寂。
要是郭翀没有这么确定的开口,其他官员都只以为是郭翀口误,但朱标亲自询问,郭翀还不改言辞。
那就说明此事为真。
真有人在科举的试卷上写反文。
李善长此刻只觉头皮发麻,连忙起身将郭翀桌上的试卷拿了过来,吴公达等官员对视一眼,也实在是坐不住了,纷纷站起身看了过去。
他们很想去看看这反文究竟写了什么,只是终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
也实在害怕牵连进去。
李善长只粗略看了几眼,脸色就陡然一变,快速将这份试卷合上,朝朱标作揖道:“禀殿下,这份试卷上的内容的确有大不敬之嫌,臣认为当即刻将此人捉拿,并彻查其同党。”
“以儆效尤。”
朱标目光微沉,并没有开口,而是伸手将这份试卷接了过来,一字一句的看了起来。
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。”
“朱明其实不爱民。”
当看到‘朱明其实不爱民’时,朱标眼中露出一抹嗤笑,道:“孤还以为是什么反文呢,原来只是一个士人的自以为是。”
“我大明不爱民?”
“陛下乃布衣出身,生来遭受了各种苦难,对于底层人可谓是呵护至极,何来不爱民之说?”
“放眼历朝历代,可有我大明这般体恤百姓的时候?可有我大明这般为万民做主的时候,可有我大明这般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的时候?”
“大明之爱民,古往今来罕有,岂容这般小人中伤?”
朱标冷哼一声。
他把这试卷放到李善长手中,并不做什么遮掩,让李善长当着众审卷官的面,将其中内容念出来。
他要一一反驳。
若是其他内容,他或许还要迟疑一二,担心传出去,引起不利影响,但说到爱民,天下历朝历代,他自认无一朝能跟大明相比。
他也是故意把这篇反文,念给其他大臣听,就是为避免这些人私下妄议,继而传出谣言,中伤陛下威名。
若是真把这篇反文给捂下去,就这些文臣士人,指不定就有人去胡编乱造,与其如此,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念出来。
彻底断绝这些人的胡思乱想。
将谣言扼杀在起步。
李善长一怔,随即明白过来,知晓朱标是何用意,心中也暗暗佩服。
若其他人遇到这种事,捂盖子都还来不及,有多少人敢有朱标这般胆量跟气度。
这种自信世间罕有。
李善长拱了拱手,淡淡的扫了几眼一旁的官员,正色道:“大明立国以来,的确蒙受了很多非议。”
“也有很多士人,感念蒙元,对大明之政多有不待见,但我朝对百姓之宽仁岂是这些人能污蔑的?”
“今日便以这篇反文为例,狠狠的驳斥一番。”
李善长喝了一口茶水,清了清嗓子,肃然道:“这篇反文,开篇便说我大明会亡于农民起义。”
“并说我朝不爱民。”
对于开篇的部分,李善长并没说几句,直接开始了正文。
“说凤阳,道凤阳。”
“凤阳是个好地方,自从出了朱皇帝,十年到有九年荒,皇恩四季浩荡荡,朱明其实不爱民。”
“洪武皇帝自开国以来,便标榜爱民之意,实则是以爱民之举,行虐民之事。”
念到这句,李善长眉头一蹙,心中也是有点慌神,这可是近乎全盘否定了当今陛下为民做主啊。
吴公达挑眉看了眼还跪在地上的郭翀,心中也不由倒吸几口凉气,若这是自己审阅到的。
只怕比郭翀还要惊恐吧。
此刻,殿内除了被要求念诵反文的李善长,坐在主座的朱标,其余臣子全都跪在了地上,双眼盯地,不敢发出丝毫声响。
朱标目光阴冷。
并没有出声,只是抬手,示意李善长继续往下念。
李善长额头已溢出了不少汗,只是并没有伸手去擦,继续道:“明兴于农民起义,也必亡于农民起义,这是历史之昭然。”
“明立国以来,天下洪灾依旧不断,粮食产量始终未增,天下卫所已趋于崩溃,卫所民户逃失严重。”
“究其根本……”
“便在于明并不爱民。”
朱标冷哼一声,却是并没有放在心上,心中亮堂,自己父皇做了什么,天地可鉴,岂是区区一篇反文就能颠倒黑白的?
他也想让百官知晓,他朱家之大明得国之正!
还是天下至正!
李善长继续道:“洪武帝淮右布衣取天下,驱除鞑辱,恢复中华,得国之正,莫过于汉明。”
“洪武帝以聪明神武之资,抱济世安民之志,乘时应运,豪杰景从,戡乱摧强,十五载而成帝业。”
“此等丰功伟业旷古未闻。”
“更因洪武帝出身平民,更懂得底层人民的不易。”
“他重视农耕、减轻赋税劳役;为减少灾荒给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,多次赈灾救济,广受人民的爱戴。”
“故大明立国之初,社会生产力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。”
“并且,洪武帝十分崇尚节俭,反对骄奢淫逸之风,对官员管教甚严,由此树立了向俭的风气。”
“洪武帝休养生息的政策,使得明朝对天下的的统治得到巩固,人民生活富足,社会发展快速,这段治理可被称为洪武之治。”
听着这一大段对当今陛下的夸赞之词,百官原本低垂的头,也不由微微抬起不少。
朱标面色稍缓,露出一抹笑意。
但郭翀听到这几句话,却是没有任何喜色,脸色更是煞白,头也彻底贴在了地上,完全没有抬头的想法。
而李善长也毫无笑意,嘴唇更是微微颤抖着,忐忑的看了眼朱标,咬牙继续念道:
“但这一切都是假的。”
听到夏之白的狂妄之言,解敏等北方学子脸色微变,‘天策’二字哪是他们这些举人能想的?
从古至今也就一人。
就这还为不少文人诟病,夏之白这番言论,若是落到陛下耳中,会让陛下怎么想?
李世民得了天策上将后,可是直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,就算夏之白是以此来夸耀自己的能耐,但这番话岂是他们这些文人能说的?
这是在给自己招祸啊!
练子宁也不由讥笑出声,前面夏之白那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,还真让他有点心里没底。
但现在。
夏之白已不足为惧。
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之徒罢了,读了一点书,知晓了一些道理,就以为自己多了不得了。
实则就一井底之蛙。
让人贻笑。
练子宁看了看四周,却是并不准备自己出风头,他家学深厚,很早便知晓一个道理。
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
这次科举能够跟他争状元的,也就花纶跟黄子澄,方才花纶接丁显的话茬,明显给他自己留下了口实。
到时暗中鼓噪一下,将那些话传到朝中官员耳中,就算花纶科考名次在自己之前,也很难成为状元。
他如今的竞争对手就只有一人。
黄子澄。
练子宁抬起左手,做八字状,抚着嘴角的八字须,眼珠精明转动着,突然,他眼睛一亮。
练子宁道:“状元不是说大话就能得到的,最终还是得靠学问说话,而今策问一试刚结束,你可敢将你的策问问答简说一番。”
“让我等开开眼?”
“也顺便看看你这自封的天策状元,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。”
练子宁略带挑衅的看向夏之白。
丁显此刻也反应了过来,脸色青一块红一块,觉得自己被羞辱了,双眼通红的瞪着夏之白。
他恼怒道:“这人就一哗众取宠之徒,哪有什么真才实学,要他拿学问出来,哪有那个本事。”
“只怕连嘴都不敢张。”
夏之白蹙眉。
他的策问的确不适合说,一旦说出来,在场的这些人都会被治罪,他还不想殃及池鱼。
也不想牵连到其他人。
他淡淡道:“大明这次科举改革之后,策问问答已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殿试。”
“甚至……”
“殿试也不重要。”
“重要的是皇帝对新科官员任选的权衡,若是殿试得赏识,可轻易就扶摇直上。”
“若是不入眼,文章做的再好,漂亮话说的再多,也终是徒有其表,难得大用。”
“你们也把科举看的太重了!”
夏之白的话一出,瞬间引得四周众人不满,怒斥声不断。
“狂妄!”
“无才无德,也敢说此大话?”
“科举乃是天下公认最为公平的的制度,岂是你能污蔑抹黑的?”
“……”
夏之白轻笑一声,放松道:“你们终究是误会了一件事,读书是读书,当官是当官,这是两件事。”
“读书使人明智,但脑子里只有着读书,只有着参加考试,然后一步登天成为官员,这么空洞宽泛。”
“素餐尸位便是我对你们的看法。”
“科举是一个更大的展示舞台,让我等能将一身所学展现在天下,为天下人瞩目,但也仅仅是一个门槛。”
“就算未曾成为举人,若就因此看低自己,反倒是落了下乘。”
“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;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”
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。”
“科举的名次只能证明自己的学问的确更好,但真正治理好地方,才更显能力,而这远比书上的学问来的重要。”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
“就算科举不中,在地方上踏踏实实干出政绩,赢得民众称赞,那早晚会为朝廷提拔重用,也为会地方百姓称道。”
“这才是为官的价值。”
“科举并不能决定一切,只是学问好的人,相较有更多的出头机会,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。”
“但这不是绝对。”
“我过去曾听过这样一句话,不要把天下让给自己鄙视的人。”
“诸君共勉。”
“北方学子或许在名次上是不及南方,但对于天下安定,恢复北方生活生产,以及弥合南北上,做出的贡献远甚于南方。”
“或许其中很多人的科举成绩是比不上南方,但他们未来的成就未必就比不上。”
“公道自在人心。”
“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,看得清那些人是真真切切做实事的,也看得出那些人是浮于人事的。”
夏之白的话一出。
解敏等人若有所思,原本憋在心头的郁闷,此刻也消解了不少。
夏之白看向黄子澄几人,嘴角露出一抹轻蔑,继续道:“至于狂妄?为何不可呢?”
“正所谓年少轻狂。”
“我夏之白年方二十二,以弱冠之龄,接连考过童试,院试,并在乡试中得到第一,为开封府解元。”
“这次科举,我同样信心十足,为何就不能轻狂,难道非得等到年老时,面对空纸,提笔一句,老夫聊发少年狂?”
“但老年的聊发,还是少年狂吗?我还会是今朝的少年模样吗?”
“尔等一个个年岁也就二三十模样,却一副老气横秋模样,终究是少了本该有的意气风发。”
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。”
“指点江山,激昂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
“……”
听着夏之白的豪情满怀,四周众人侧目,也是升起一抹肃然之意,相较夏之白的自信捭阖,他们的确是有些太过迂腐了。
也太过死气沉沉了。
夏之白又道:“这次科举是停止十年后再开,若是不出意外,朝廷这次选拔的官员会比寻常多不少。”
“我等的确年纪尚浅,资历阅历相较略有不足,但假以时日,我等未尝不会成为天下的中流砥柱。”
“如何不该自信?!”
“我们今后可是能影响到到天下的走向,若是连这点信心都没有,又谈何去做个好官,为天下人造福?”
“另外,练子宁你的小心思太多了,工于心计,却无远见,你既想让我出糗,那我便跟你们赌一场。”
“以我的性命为赌注,赌你们花练黄,最终无一人成为状元,你们可敢跟我定这个赌。”
朱标猛地站起身,脸色怒红,眼中久违的露出了一抹不安跟紧张,仿佛真被这些话激怒中伤了。
赵瑁等官员对视一眼,眼中都露出了一抹惊惶跟淡淡的恍惚,全都垂着头,没有再开口,如今的场面,不是他们能开口的了。
任意一句话,落到朱标耳中,都可能变成火上浇油,亦或者变成是在指桑骂槐,他们入朝多年,深谙为官之道,自不敢以身犯险。
只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。
这篇‘反文’说的一些话,的确有几分道理,大明相较其他朝代,立国之初,的确太严跟太死板了。
毫无变通。
完全只能由着陛下的想法。
大明当初之所以停办科举,除了选拔的士人良莠不齐、不堪实用外,更大的原因,还是这些士人,对于大明并无认同之感。
大明立国之初,天下的士人,对大明很多都持着观望、怀疑甚至是敌对不合作的姿态,很多士人也根本不愿出仕仕明。
究其原因。
便在于陛下对待科举制以及士大夫的态度,天下的儒生,在陛下那都得不到真正的亲近跟实心委任。
而这或许真就如这篇文章所说。
与陛下的出身有关。
当今陛下对贤才的渴求,很早就表露了出来,为吴国公、吴王时,便发布了‘兹欲上稽古制,设文、武二科,以广求天下之贤。’
但求来的贤能之士,并不能人尽其用,也不能真如诏书上的那般得到重用,反而被百般挑剔。
陛下多次以‘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’且不堪实用,无法‘以所学措诸行事’,指责这些官员,无法实现陛下想要的‘责实求贤’。
陛下的确有很强烈的求治国贤才之心,但陛下要的所谓治国贤才,只是想让这些人去按陛下的想法做事。
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跟心思。
只让其为自家家奴!
这就当真如农人一般,很想要得到他人的帮助,却又很担心别人惦记上自己的东西,故始终怀着极强的戒心跟提防。
稍有不满,便粗鲁的用强权的形式压制,以做威慑,以防贼的心态去用人,又如何能让人心安?
朱标冷冷的看向下方百官,冷声道:“你们也认可这些话?”
李善长拱手道:“回殿下,臣只听到了对陛下的污蔑,此等大逆不道的言论,当杀!当诛!”
李善长一脸怒气,仿佛真为朱元璋在打抱不平,义愤填膺。
朱标冷冷的看了李善长几眼,又看了几眼下方沉默不语的百官,脸色已阴沉至极。
他又如何看不出,这些官员的心思,分明是对这番话有认同,也真以为当今陛下有的决策有错。
只是他很费解,既然百官对陛下的一些决策有不同看法,为什么就不敢说出来?
李善长满心忐忑。
已不知自己该不该继续念了。
只是一脸恳切的看向朱标,想让朱标拿个主意。
朱标脸色变了又变。
最终。
他消瘦的脸颊上恢复了一抹血色,也重新恢复了寻常的淡定自若,淡淡道:“继续念吧。”
“孤也想听听,在这些乱贼口中,我大明还有哪些积弊?而且孤从不认为大明尽善尽美。”
“错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”
“这也是孤一直以来的态度。”
“念。”
朱标展现出了身为储君应有的气度跟豁达,也彻底扭转了想法,不再只是将这篇文章视为反文。
而是视作一份谏书。
李善长犹豫了一下,继续道:“洪武帝对为给自己办事的官员,尚且如此苛峻?何况是对百姓?终是假以爱民之举,行虐民之行罢了。”
“空有爱民之心,无爱民之举,具天下为私有。”
“由此观之,明得于农民起义,也注定会失于农民起义,只不过是从开局的一个碗,换来结尾时尸体的直硬罢了。”
“以治家的方式治国,只会越治越差,越来越残暴不仁,因为‘忤逆’的臣民,只会越来越多。”
“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,只教臣民一味的顺从,一味的去遵循所谓的祖宗之法,最终只会将天下带入到无尽的黑暗深渊。”
“民不聊生!”
“洪武帝为何对民如此注重,甚至三言两句都不离民,非是真的对民报以宽怀,而是只懂得民。”
“或许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,洪武帝学了很多的谋略和军事,但对于具体的儒家六艺,涉猎并不完整。”
“士农工商兵,只知晓农兵。”
“因为懂农,所以对农业相关抓的最紧,而对于其他,则只能延续着旧制。”
“很多时候非是不想改,不想变,而是不知道,不敢,怕被骗。”
“更担心为大臣蛊惑诱骗。”
“因出身的缘故,洪武帝对于其他的社会阶层都充斥着敌意,认为其心怀不轨,也始终抱着最大的恶意去揣度,这其实不算大问题。”
“但为君不同。”
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”
“更当权衡朝堂,以天下为重。”
“非只有农、民。”
“世间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,世人大多无利不起早。”
“要么图名,要么图利。”
“而最终的决定权,一直都掌握在当权者手中。”
“然洪武帝却连选择判断的机会都不给,只视百官为其长工,万民为其奴隶,想世代供其驱使。”
“长此以往,天下只会充满谄上欺下者,官员懒政庸政懈政的情况,会进一步扩散。”
“因为多做多错,少做少错,不做不错。”
“与其如此。”
“何必给自己惹麻烦?”
“正因为此,大明立国十几年,除了重定天下秩序,天下各地的矛盾依旧充斥,利益不均,未来不明,人心浮动难定。”
“尤其洪武帝喜欢以强权形式,粗鲁的对待天下臣民,如此情况下,人人自危,朝不保夕,大明又岂会真有长足的进步?”
“贾谊所写的《过秦论》中,有这么几句话。”
“践华为城,因河为池,据亿丈之城,临不测之渊,以为固。”
“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,始皇之心,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”
“这跟大明的做法有何异同?”
“以一人而定万世之事,又岂能得到好的下场?”
“只是在重复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“奈何奈何。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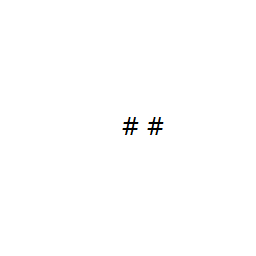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